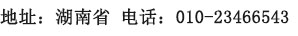赵东简介
赵东,安徽省泗县人,博士,副教授。从事文艺理论和区域文化产业研究,擅长现代诗歌和民族文学艺术研究。写诗多年,有少量诗歌发表,提倡新乐府和漩涡主义诗歌写作理念。
站在戏仿的一边
北魏
赵东陆陆续续发来他的诗,开始是戏仿之作,后来是几个长的,再后来看到阿尔在一篇诗评里提到几首他早期写的诗,他又补充过来,几次来回,我反而感觉赵东这个人让你看不清楚,像个隐士,衣着随便,他在众人中你绝对不会注意到他,而你一旦注意到他,你也会很快把你的眼光移到他处,只有他愿意(不是你愿意)跟你说什么的时候,你才注意到你先前的失礼和眼拙。他对写诗也是这样,你不能看他“丢三落四”的样子,就觉得他的诗不怎么样他自己都不重视才丢三落四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是的,他在诗的表达上也是“丢三落四的”,这恰恰暗合了诗的另一个境界——随性和放松。现代主义诗歌让我们紧张的太久了,弄得我们就像一群惊弓之鸟,无处可藏,在意象的天空上,到处飞,又无处可去。
赵东作为受过专业训练的青年诗歌批评家,对当下正在发生的中国诗歌走向思路非常清晰,认识独具一格,我以为这得益于他不间断的诗歌写作。我这里所指的不间断的写作是指在先锋意义上的写作,是围绕着“破”而向后的诗歌写作,而不是空谈。你看不到他跟你跟这个时代有什么关系,但他又能让你处处感知这个关系。他没有刻意隐藏什么,他采取的方式是“戏仿式”的。这种“戏仿”我理解是,他可能暂时还不想把他的内心敝开,但他已经通过他的“戏仿”在展示了他的内心。在戏剧性表达上,他是没有保留的,这是我喜欢赵东诗歌和他为人的地方,也是我信赖他的地方。因为他的这些诗歌你看到的是,赵东魔术般的从现代主义挣脱的不留痕迹,你更看到了他在汉语诗歌自生性上的率性表达,可贵的是他的这种表达一点也不让你难看。
认识赵东不少年了,赵东的温润慢语给我留下好印象,不像我,两杯酒下肚,声音的分贝上去了就下不来。有一段时间我们交流频繁,所谈大多集中在诗歌上,我受益匪浅。通过赵东,我还神交了他的诗友阿尔、许光等,这些都是在诗歌这条“黑道”上,到了黄河也不死心的人,我仿佛看到他们看到我头破南墙时,一个个也把头破在了南墙,我引为知己,并幸慰有这样一群行走在淮北平原上的“诗歌汉子”。
.9.21
赵东诗歌16首
表叔
表叔用一个指头拿起棋子
轻轻向前推了一步
我抬起头看看他
车在马口呢
没注意吧
表叔好像没听见
学过拳击吗很有用的
十年前在阜阳三监狱
我用飞踹把一个打拳击的撂倒
趁年轻学学拳击
我嗯了一声表叔自幼在山东习武
三五个人不能近身
练就一身红砂掌的绝学秘不示人
那匹倒霉的马蹦跳着走开
表叔的炮口正对着我的老巢
炮也在马口呢危险
表叔没有抬头拿起另外一匹马
漫不经心的放在河界
出拳如闪电回拳似火烧
上个月在集市上
三个年轻人被我打倒
没看见我怎么出拳
现在的年轻人啊
一生
4秒是小刘节目的长度,小刘的戏份不到1秒他夹在两个刑警中间,像一个猥琐的奸细可是他刮了胡子,剃了光头,显得比平时干净
女神般的播音员,嗓音像飘荡的鹅毛“该犯用绳索将女友捆绑,企图实施虐奸,被女房东撞见,因害怕事情败露,将女房东当场掐死并将尸体埋在租住房的床下。”
镜头转换,是小刘的卤菜摊和出事的那间租住房我早晨跑完步就会在小刘那里买上半只板鸭或几根鸭翅刘记无为板鸭远近闻名,小刘一看见我就喊“赵哥早,今儿吃点啥,”“半只鸭子,不要头。”“半只鸭子,再送您两根鸭翅。”
小刘是南方人,善于经营,一分钱不嫌少,一百万不嫌多卖水果的水莲说“刘哥的生意真是太好了,好崇拜哦”小刘的菜刀舞得更欢,“跟了哥,钱都是你的”
镜头再次转换,小刘的女友一身纱布和石膏她的眼里很空洞,“要他别碰那个,他偏不听。”
女神播音员的那根鹅毛还在飘:“据法医鉴定,遇害的女房东死前也遭受性侵害,该犯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当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老潘老潘吸烟有功夫一支烟吸半个钟头不灭他常笑嘻嘻的对我说这叫功夫年轻人学着点更绝的是老潘只吸半支烟剩下半截直挺挺地插在花盆里我说老潘别人种花你种烟啊老潘笑而不答好像充满玄机行将凋残的花朵和吸了一半的香烟站在一起像一群被腰斩之后的尸首“潘海波同志因病去世享年73岁……”以前在车库值班室里他喜欢把自己站成一根木桩呼吸匀长沉肩坠肘松腰圆臀现在站在车库的公告栏里双臂抱圆十指相对两腿微微开立
小丑
小丑蹒跚着走上台
四下寂静无声好像空无一人
小丑左右看看嘴角抽动一下
好像是哭又好像是笑
小丑在怀中虚抓一把
人群中一阵窃笑
看他有什么花招一切都是假的
小丑手中多出一根小棒
他把小棒放在舞台中央
口中念念有词
小棒越长越大直插云霄
观众伸直脖子仰首遥望
小丑做个鬼脸抱着柱子爬上去
一会儿钻进空中大家着急起来
纷纷打盹聊天上厕所
忽然灯熄幕落
众人还来不及眨眼
一切已经恢复原状
小丑还是小丑小棒还是小棒
顿时掌声如雷人群雀跃
小丑施展开来好像
擎着一面猎猎作响的旗帜
小丑人棒合一无处不在
上下翻飞气韵生动
世界再也按捺不住了
看客们跺脚呐喊尖叫挥拳
膜拜者抑郁者癫狂者神志不清者
突破警戒相互踩踏
小丑不闻不顾一味狂舞
舞台一片大乱
人们高喊口号抓住小丑把他撕碎
一个声音从空中传来
亲爱的这不过是一场戏
人们顿时醒悟过来羞愧难当
呆立在舞台上
魔术
你所见的一切并非真实
魔术师的手凌空向我抓来
我屏住呼吸仿佛他正
握着一条丝丝作响的蛇
这场景让我想起那年早晨
一队威猛雄壮的士兵
走过我家门口我指着黑魆魆的
枪管说我要我要我要
母亲小声说小心被他们带走
魔术师忽然转过身去面对观众
手中凭空多了一枚绿色纽扣
它被小心地安放在我胸口
好像它一直都在那里
我松了一口气
魔术师忽然对着观众高声说
看看你们的胸前
大家恍然大悟中低下头
每个人都多了一粒绿色的纽扣
苍蝇
门口坐吧凉快哥哥蹒跚着要去搬板凳不用蹲一会就走我膝盖弯了一下在他面前矮下来不争气的屁股却向后翘着他斜着身子在石墙边坐下来小心地从鞋里拿出双脚长长伸直家里还好吧今年阴天多他盯着发炎的脚趾说几只苍蝇在他脚边盘旋不时有几只降落在伤口上孩子的事情办好了吗他漫无目的地挥着双手好像在赶苍蝇
树桩
两道河叉的交汇处
树桩夹杂在大片灌木丛里
它本来是一株树
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它变成树桩
这一点从它折断后留下的新鲜伤口可以看出来
如果再早几天你还能看到它原先的那大半截
像一条粗壮的大辫子耷拉在旁边
猛一看好像一个人被砍了头脑袋却不掉下来
前天一个过路的老农把那半截扯下来拿回家当柴火
树桩现在看上去很矮小
一副默默无闻的样子
其实不然毕竟它曾经是一株伟岸高耸的树
鹤立鸡群地俯视众生这么多年
它知道怎样一览众山小
它知道这些草啊花啊荆棘啊
成不了大气候
只要一阵风一场雨
就要了它们的命
树桩表面上和它们混在一起
其实它根子不在这里
你要是戴上眼镜仔细观察
风雨剥蚀后树根已经裸露出一部分
那些树根像一团扭曲的蛇盘结在一起
有的粗如手臂有的细如麻线
那些树根不是平贴在地面上
而是拔地而起像一只凌空展翅的鹰
这些大小不一的根茎坚硬如铁交相呼应
有的地方特意留下空白
大概恰好能放下一只脚或一颗脑袋
既可以作为风景留给风骚之士审美
还可以让不怀好意之人自入陷阱
很少有人知道
其实这些根系动辄绵延数百里
大口吸食保存了上万年的新鲜空气
不管是风沙涝还是大旱金石流
地震海啸山崩地裂都毫发无损
就算一场野火烧到这里
一阵春风吹过
它们又会兴高采烈地活过来
途中记
先上来的是高个子后上来的矮个
站在下面的是一张油光水亮的大脸
旁边那个笑容凝固在脸上像结了冰
下次回来就过春节了多少钱一张票
二十没涨才七点太阳就这么刺眼
一条大河从身下闪过两只水鸟翅膀宽大
你不是安徽人,到娄庄了,七点二十到灵璧
那个女的家里的烟酒都是真的她信耶稣
心好她对人好人对她好
到泗县还是灵璧这是虞姬你看
那里是“迦南超市”这里是虞姬墓
很快就到你下个月到重庆成都还是重庆
重庆柏桦的家乡火锅棒棒他现在成都
柏桦诗写得好就是节奏太慢闷
其实都是过程把细节弹射进感觉把感觉弹射进细节
商雨月底说要来宿州到时候叫上阿尔喝两杯
酒不是好东西少喝点再不行大家喝茶聊天
诗就那么回事别太当真不能太认真
现在好了常来常往这条路叫汴河路
前几年车开到家门口都不知道
现在我有两辆车越有钱越有钱
哎十年了孩子找男人伤心到家了……
隐士
那种一个人的感觉又来了,特别在冬天越发强烈,
最近她形成一个习惯,老是偷偷摸一下左手的小指头
再低头不经意的看一眼,还喜欢站在黄河故道,
让风吹透她的身体,那个感觉从骨头缝里钻出来,
很强。
她夜里咬牙,咯吱咯吱像在嚼着什么。
她说有一个影子老是来烦她,
她是笑着说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甚至有点调侃的味道。
其实也没什么了,只要让自己傻一点,影子就会自动消失。
她大声谈起最近看的一本书,
说里面有个穿红斗篷的人像斗牛士,
娶了两个老婆,一个白的一个黑的,一个聪明,一个愚钝。
你喜欢聪明丑陋的还是愚钝漂亮的,
其实都一样了,黑的白的都无所谓。
那个听话的人,托着下巴像个思想者,
黑的白的确实都一样,只要关了灯。
呸,下流,白马非马不是传说,
漂白剂、晒太阳、植皮手术、外科整形、变性激素,
她只是在掩饰罢了。
她没有提及的那些形象,排成一座蛇阵,
以最急促的节奏扭动腰肢,什么速度最快,
是小提琴还是钢琴,总之是弦乐器,
大弦嘈嘈如急雨,告诉你吧,答案是琵琶。
她忽然不说了,被看穿一切的沉默,
你要到哪里去,印度?西藏?
一起去吧,怎样?
他抬起头说:“你听说过天葬吗?”
两个孩子
DD知道被“他”盯上了几个晚上睡不好DD急着上厕所厕所灯全坏了黑胡胡的很吓人DD知道这下完了肯定要出事赶紧跑去找姐姐帮忙姐姐一家人睡得很死门也插的死死的DD憋不住了飞快跑回家冲进厕所小便刚解开裤子厕所的灯齐刷刷亮起来淋浴喷头里射出滚烫的开水DD哭了DD知道是那个小孩干的好事他的小脸红红的很可爱的样子他背后有个穿深蓝色制服的人有时笑眯眯有时很凶狠DD去找红脸小孩屋里站着的是个白脸小孩DD喜欢白脸小孩他们玩堆土的游戏堆下宽上尖的大土堆红脸小孩跑进来一把抱住DD的腿“我要你和我玩,我家有苹果。”DD看一眼白脸小孩,
神色镇定,心情平静再看一眼红脸小孩,
面色阴鸷固执DD一下子全明白
“去你妈的,老子摔死你。”红脸小孩变得凶狠起来死死箍住DD的身体DD拼命挣扎蓝衣人走出来皱着眉头
好象整天思考问题似的红脸小孩和蓝衣人逼过来“你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人要服从命运的安排。”DD像条发疯的狼狗眼睛里是恐怖的血丝抄起木棒抽打蓝衣人蓝衣人身体硬邦邦的
发出结实的响声红脸小孩更冷漠凶狠紧紧贴在中年人的身上DD忽然想到
出奇制胜的一着插眼、踢裆、锁喉……DD终于咬破了自己的舌尖一口鲜血向中年人喷射过去中年人措不及防满脸血污DD拼命扑上去竭尽全力砸过去……
又见镜中
地震山体破碎满眼是猛兽的体毛
青铜钥匙从锁眼里看到微凸的腹部
东南方是最好的一栋早晨的阳光明媚
头部向后微微仰起的美酒拗过去拗过去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秦罗敷
虎口唇边未擦干的血丝营养过剩
河道淤积搁浅的季节又来了
任由疯长的头发只剩猥琐的头皮
银屑病无法根治专治梅毒花柳的电线杆
又来了来自底层的臭气无法根治
大肠嘲笑小肠大国愚弄小国
血脉喷张的原子弹日本已经投降多年
又来了满眼是金黄色的军刀
门打开了满眼是餐厅和猛兽的气息
蓝色的证件不消说打火机蓝色的火焰不消说
制服硬领硌着僵直的颈子雨夜的皮靴不消说
烧烤里宿醉里呕出一个新时代骄傲的小胡子不消说
看官仔细毛孔阻塞血管阻塞尿道阻塞肠道阻塞
汽车时代已经来临电子音乐时代已经来临
膨胀的肚腹陷在沙发里胆管肿瘤在膨胀
美元在膨胀水壶在膨胀松垮的裤带在膨胀
在膨胀的时代食品添加剂在膨胀
这是最好的一栋东南方钢筋水泥在膨胀
献歌(选二)
太阳升起
新的一天来临
而我们
活在诗的另一面
歌师黄老牛
黄老牛是我见过最老的歌师
我听他唱过亚鲁王
歌词关于亚鲁祖先征战迁徙的历险过程
我听不懂古苗语
金戈铁马的场景却历历在目
早在十年前黄老牛已经备下骏马
准备在百年之后骑着它
手持长刀头戴铁盔
冲破天地束缚
回到祖先的家园
神奇的是黄老牛和那匹战马
黄老牛越活越年轻
战马却不断老去
黄老牛不得已换了坐骑
如今已是他的第三匹宝马良驹
黄老牛还是那个威风凛凛的将军
唱着那首古老的亚鲁王
年猪
新年预示某些事物的终结
这不是我的噩梦
这只是我的宿命
四个壮汉把我推向刑床
来不及想这一生有多少春梦
我不情愿地四腿张开任人宰割
四双大手几乎将我的腿筋撕裂
平常他们只需一人
或将电棒藏在背后
只消在头部轻轻一触
顿时世界无比清凉
或用铁棒猛击猪嘴
趁着疼痛之时对准脑门狠狠打下
片刻之后便是永恒超脱
我见过各种刑罚
有剖开肚腹
将各种污秽之物暴露于世
有割下头颅
将身体变成一堆无魂皮肉
恰逢岁末
酷刑更加艺术
头上打上花刀宛如祭祖的牺牲
肚腹吹足气体便于剥皮去毛
四肢小心卸掉骨头仔细剃净
作为一只年猪
我的命运就此完成
相遇
冬未必冷
春未必暖
冬与春相遇在墓地
我们常在这里相遇
有人声称在这里见过鲁迅
冬行夏令
或是四季混乱
你的穿着看不出季节
我在墓地等候已久
你跑过来
大口喘气
一见面就脱衣服
脱了一层又一层
棉袄马甲衬衫T恤背心
棉裤秋裤衬裤内裤
她通体透明
原来身体便是衣服
她拿起一把铁锹
用力挖起来
我拿起一枝敦实的铁杵
在洞穴上雕刻
他又拿起一把铁锤
叮叮当当敲打一块巨石
我换了一枝尖利的铁笔
在石头上写字
清晨的阳光照过来
洞穴上的壁画活了
游龙走兽鱼精花妖
千万匹烈马驰骋草原
她的身体越发澄澈晶莹
我在她身上写字
在她体内雕刻
千万条河流从她体内涌出
千万座高山从她身上长出
风吹过来
雷雨升腾
于是我在石壁上刻下
某年某月某日
风雨大作
表达
一群鸭在阳光下摇摇摆摆走过
扭着屁股十足的一副鸭样
把薄如蝉翼的脚丫子
如履薄冰地放在舞台上
看上去大了点仔细分辨
每个脚蹼之间都有精致的领地
多么绝妙的三寸金莲啊
趁着黑暗好下手
从底下狠狠摸一把感觉真是好得很啊
好戏开始了
大幕下面站着几只畜生
鸭兔猪狗猫羊牛
饰演学生教师警察医生病人厨师官员外国人
剧情简单至极
洪水即将来临诺亚方舟已经造成
可是空间有限只有幸运儿可以登船活命
观众就是上帝票房就是目的
至于这些畜生
来自尘土终将归于尘土
主持人从天而降手握指挥棒
他从裤裆里摸着一块五色石
这定音的破石头又臭又硬声如洪钟
难道黄钟大吕就是这个玩意
天下大势鼎足之形成
只有五人可以登上方舟
拿出你的民主和勇气
勇敢说出心中的判决
观众纷纷举手表决
第一个被否决的是病人
在古罗马也是如此
身体孱弱的儿童被扔进山谷摔死
西方强势皆源于此
第二个被判处的是外国人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党同伐异以貌取人世人皆醉我独醒
蒙古大军横扫的伟绩堪比八国联军两千多人的凶残
第三个被驱逐的是教师
只有衣食住行才最接近人类本质
人类抢夺食物的历史教师不在其列
观众舒了口气
在醉眼朦胧中享受杀人的乐趣
狡猾的主持人宣布
受天气影响方舟只能乘坐二人
还要继续杀死三人
第四个死去的是警察
韩非子死于李斯之手
李斯死于自己发明的腰斩之刑
(嘻嘻这才叫法网恢恢)
第五个倒霉的是学生
北大教授钱理群称之为精致的功利主义者
他们致力于电子设备的淫乐
精心钻研登龙之术的奥妙
殊不知小年不如大年小知不及大知
(好一个雅思托福的牺牲品)
第六个受牵连的是官员
千里当官为了吃穿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待到清算之时金钱女色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早知道太上感应篇是官场必备之书)
剩下的那两个席位
聪明的你已经猜出
剧本就是这样写成
只剩一个名额可以逃出生天
最理想的职业是什么
马克思曾在中学毕业论文中写道
要献身于人类最伟大的哲学事业
马克思后来又写道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好了拿起你的快刀
取了那医生的狗命
李逵大喊吃俺三百板斧
好戏即将落幕厨师完胜诸神
观众皆大欢喜世界如此安宁美好
除了唇腮之间的啃嚼之声
还有齿间血肉飞溅的盛况
这出完美的大戏就这样在一座
乡村的草台班子完美收场
狼
乖,你们好好听话,再说外面风那么大,又停电。一千年没用过的油灯都拿出来了,这灯是柴油发动的,最近柴油紧张,只好加了汽油。
今天给你们讲个爱情故事吧,爱情,你懂的,我知道你们喜欢。外面果然刮着风,风打着旋,像几千匹狼在嘶嚎。从前有个女孩子,长到十几岁,一直被父母亲关在闺房里,有一天跑到自家的后花园,看到很多美丽的花,于是就爱上一个书生,后来就害相思病死了,后来又活过来。嗯,这个还不好,那换一个吧。
她的影子在油灯下拉成细长的一根线,浓密的毛发遮住半边脸,一副旧时文人的轻狂模样。旷野里几万株树木乱发飞舞,像几万匹烈马在奔跑。
从前有个女孩子,长到十几岁,父母亲都死了,被送到亲戚家里,爱上了女里女气的表兄,后来这个表兄娶了他的表姐,后来这个女孩子就死了。这个也不好,那说个意大利的爱情故事吧。
她扭过头,把书页翻得哗哗响,黑黢黢的手背举起来又落下去,带起油灯的火焰噗噗地跳。从前有个女孩子,她爱上了一个仇家的英俊公子,这个公子杀了女孩子的表兄,后来,男孩子和女孩子都自杀了。这个还不好啊,那就不讲爱情,我们谈谈人生吧。
狂野的风纠集着土块和沙粒,泥沙俱下,眼看着小屋摇摇欲坠。她转过身子,她的腰部向后面弯成一张弓,伸出一根细长的指头,用尖利的指甲在墙上快速的一划,变魔术似的刻出一个大字“天”。好了,现在请跟我念,“无……呜呜呜呜”,窗外的风声越来越大,从各种缝隙钻进屋里,油灯猛地惊醒了,刺刺地向外喷出灯花,一粒油火落在她的胸前,她的胸部陡然隆起,露出两颗乌黑的乳头。
那我再说最后一个故事吧,从前有个小女孩,到外婆家去,结果外婆被一只狼吃掉了,那只狼变成外婆的样子,最后把小女孩也吃掉。
一阵风吹进来,她的毛发被吹起,露出两排白森森的牙齿,不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像是在磨牙,又像是在笑。告诉你一个秘密,这间房子是纯铁打造的,密不透风,用上千年都不会坏,十级地震都不怕,现在到处都在地震。哼哼,信不信,只要我一口气就可以把它吹倒,外面的大地在剧烈的抖动,水也在动,山也在动。她站起来,变得更加细长,粗大的毛孔像一根根钢针向外扎开。她拉开衣襟,猛吸一口气,胸毛陡然竖起,对着虚空干笑一声,逆我者死。告诉你们吧,反正这孩子一生下来就是要死的,早晚而已。在她回头的瞬间,她的眼里布满血丝,暴突的眼珠里发出绿油油的光,有一滴绿色的眼泪快要掉下来。
我们不定义先锋诗歌
我们只展示先锋诗歌文本
主编:北魏
副主编:丑石、赵东、梁震、袁魁
编辑部主任:风儿
设计总监:上谷阿凡
定期推出日:每周二、周五
投稿邮箱:shijiesan
.